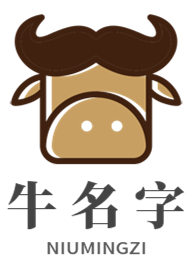老皇帝竟然对她有非分之想,为了捍卫自己丈夫的尊严,他开启夺嫡争权之战,只为夺回她
岑樱展目看向枝叶未落的大树,透过它,一直看向了树木之上的蔚蓝天空。
明年的她还会在这里吗?
她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地方。
从前只听说京都洛阳是何等的轩敞华丽,可到了这里之后,她与阿爹分离,连闷罐儿都要另娶他人了,娶的还是她唯一的朋友……
她不喜欢这里,她想回家,想回到过去在乡下和阿爹和闷罐儿还有阿黄在一起的生活,很想很想。
如果,如果闷罐儿不和她们回去,她就自己和阿爹走好了。反正他要娶那么多的女人,她也想散了算了……
女孩子久久地看着院中花树,眉目黯然,一袭鹅黄襦裙在晚风中微微舞动,有如梨花开在月下,冷浸溶溶月色,清新闲适,淡远出尘。
皇帝一直侧眸看着她那与生母十分肖似的眉眼,秋阳自树梢照下,照得他不复年轻的清俊面庞上,竟也有了些许温润的假象。
樱樱,樱樱。
其实不必卞乐找来当年的宫人与太医确认,他又何尝不知她是谁的孩子。
樱樱的名字很可能是永安取的。她给这个孽种取名为樱,偷天换日地也要将她送出去,却杀了她和他的孩子……
倘若这是他的女儿,她还会这般在意这个孩子么?答案显而易见。
沉寂了十余年的怒意与怨恨重在胸腔点燃,如同毒蛇吐信,又似烈焰狂舞。岑樱忽觉身侧寒气凛冽,不明所以地侧过眸来,皇帝已恢复了和煦慈爱的面色,道:
“樱樱,阿舅累了,扶阿舅进去吧。”
这并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,岑樱领命将他扶进了寝殿。皇帝神色和蔼:“天色也不早了,你也回去吧。明日,记得来陪阿舅下棋。”
“是。”岑樱婉婉施礼,随后退了出去。
她入宫已经七天了,这七日里,圣人除了偶尔叫她作陪、说一些母亲的事,倒也没有再如那日进她房间一样的不合常理的举动,渐渐放下了戒备。
皇帝一直目送着那道纤瘦窈窕的身影消失在廊柱日影间,神情如怔。直至卞乐从殿外走进。
“叫你去办的事,还没有办好吗?”
他问,面色已不复方才的温和。
卞乐面露难色,战战兢兢地应:“……回陛下,这件事的确有些棘手。尚宫局已经在尽全力寻找当年放出去的宫人了,想必不久就会有回讯……”
“你的不久已是三个月了!你们都是废物不成!”皇帝龙颜大怒。
卞乐吓得身如抖筛,赶紧跪下:“陛下息怒!息怒啊陛下……”
皇帝胸腔中血气上涌,目眦欲裂。
说起来,这件事,也的确是他的错。
当年稳婆告诉他,永安生下的是个已经足月的女婴,并非七月生子的早产儿,算着时日,刚好是她还未与裴公瑜分别的时候,所以才能够笃定她是裴氏之女而非他的。
为掩人耳目,在场的宫人、御医、稳婆几乎被他杀了个干净。如此一来,如今要想再找到幸存的、已经放出宫去的当年侍奉过公主的宫人,确实难了些。
但他想,当年母亲都能将岑樱换出去,这其中必然还会有漏网之鱼,这才命卞乐去查宫人名籍,试图找到当年的知情者。一连两个多月过去,却都未有任何的蛛丝马迹。
他最终长叹一声:“建康的谢宅去过没有?可曾找到谢云因?”
谢云因是皇帝的表妹,精通医术,当年在宫中陪伴皇帝的母亲肃宗谢皇后,也曾去探望过永安,自是知晓她的孩子是否足月而生。
谢家毕竟是他的母族,他并未动谢家,只是削权而已。谢云因也回了江南,后来他派白鹭府去查探过两次,听闻是在民间行医。
“回陛下,谢娘子两月之前往九华山采药去了,恰好是在我们的人赶去以前,所以暂时还未有消息。”
皇帝怒气稍平,无奈地叹了口气。
知道在哪儿就好,总好过凭空消失。
关于岑樱的身世,他十分笃定岑樱不是他的女儿而是裴家的,但事关人伦血脉,不得不慎重,他已经等了两个月,就……再等上一会儿吧……
*
丽春殿里,岑樱一觉睡至了辰时。
她昨夜想父亲和夫君想得哭了半夜才睡着,今晨起得便有些迟了,直至宫人们往殿中搬东西才醒了过来,揉揉眼从床上坐起,还有些犯困地呢喃:“你们在搬什么啊……”
见她醒来,一名小宫女忙放下手中的活计:“回县主,是陛下怕您在宫中无聊,派人搜罗了好些话本子来。”
“您要起来吗?奴服侍您洗漱。”
那宫人一张圆圆脸儿,十分殷勤和善。岑樱觉得她有些眼熟,但未多想,微红了脸支支吾吾道:“……我自己来吧。”
她本是乡下来的野丫头,不习惯被人伺候,拿过衣裳欲言又止地看了那宫人一眼。
宫人会意一笑,退出殿去:“那奴就先下去了。”
“奴叫青芝,县主有什么吩咐叫奴一声就好了。”
殿里,岑樱慢腾腾穿好了衣裳,洗漱后用了些早膳,便去到外殿的书案下翻阅卞乐送来的那些话本子。
时下流行的多是些怪力乱神的故事,岑樱胆小不爱看,就丢开了。正翻找着,宫人来报皇帝来了,忙随手将书放在案上起身去迎。
“樱樱在看书?”
皇帝走进来,笑着问。
岑樱不好意思地抿唇笑了笑,皇帝又拾过一册丢给她,在书案旁的矮榻上坐下:“朕也好久没有看话本子了,正巧,你读来给朕听听。”
那册书的书名是《汉孝惠皇后外传》,看着像是册人物列传。岑樱不疑有他,屈膝跪坐,展开书本,当真清声朗读了起来。
“汉孝惠皇后张氏,名嫣,字孟媖,小字淑君。惠帝姊鲁元公主之长女也。”
“阿嫣当五六岁 时,容貌娟秀绝世。时帝方议立后,欲访名家贵族之女容德出众者。太后谓帝曰:‘阿嫣帝室之甥,王家之女,天下贵种,实无其匹。且容德超绝古今。吾选妇数年,无逾此女……’”
她诵书之时,皇帝就一直出神地看着她,目光柔和,脉脉含情,仿佛是透过这具年轻的躯壳又陷入了久远的记忆里,望进另一个灵魂。
岑樱一心只在话本上,并未察觉他怪异的眼神。越读却越觉不对劲了起来:
“帝曰:‘如乖伦序何,且彼年尚幼。’”
惠帝说,这是否背离人伦,况且阿嫣尚且年幼。
“太后曰:‘年幼不当渐长邪,且甥舅不在五伦之列,汝独不闻晋文公之娶文嬴乎?’帝乃从命,诏群臣议纳皇后礼……”
吕后说,年纪虽小但会长大,况且甥舅不在五伦之列,你没有听说晋文公娶文嬴之事吗?惠帝于是从命,召集众大臣商议纳皇后礼……
如若她理解得没错,这话本,是在讲舅舅娶了外甥女……
后面的文字,则是在讲张嫣嫁与舅舅之后的种种生活,不管是话本中的张嫣和舅舅本人,还是写书之人,都对这段有违人伦的婚姻未有半点不认可。
岑樱心头疾跳,越读越迷惑,声音亦渐渐小了下去。
她迅速将书册浏览至尾声,当目及惠帝娶了张嫣、惠帝和张嫣的闺房之乐时已是唬得浑身乱颤,如坠冰窖,战栗不已。
她几乎是颤抖着丢开了书,不肯再读,皇帝微微眯眸:“樱樱怎么不读了?”
“我……”她艰难地张口,声音颤栗似哭。
脑中还残存着文字描绘出的绮艳画面,岑樱只觉得可怕,汉惠帝是张嫣的舅舅,舅舅和外甥女,怎么能成婚?
还、还把她抱到膝上,数她的牙齿,后来又、后来又看到了她的,她的……称赞肥白……
这种书,怎么能给她看?陛下为什么要叫她读这个?
岑樱羞得脸颊通红,五脏六腑皆似烧起来。当看到皇帝落在自己身上的眼神,心中又是一紧。
圣人看她的眼神,贪欲,淫邪,痴迷……全都一览无余。
她曾在胭脂山的阴暗山洞里看见过这样的眼神,一点儿也不陌生,她知道这代表了什么。
可圣人,是她的舅舅呀!他怎么能!
联想到方才他叫她念的书,岑樱鼻头一酸,险些掉下眼泪来。却只能跪伏下去,嘤泣着谢罪:
“樱樱殿前失仪,请陛下恕罪。”
她想要离开这里,一刻也不想多待,却怕激怒了他阿爹也落不得好,再害怕也还残存了一些理智。
又突然很想念她的闷罐儿,他会保护她,就像山洞里的那次。夫君……闷罐儿……她真的好想他呀!
这样的防备与抗拒,无疑是一种无声的拒绝。皇帝的脸色渐渐变得阴沉,他看着身前跪伏的少女,缓缓站起身来:“樱樱,朕的意思,你当真不明白吗?”
却没有明说。
她的身世一日不明,他就一日无法真的下手。但他等了这样久,此刻又听了这样久的香艳话本,的确是有些不想忍了。
他甚至想过,就算寻回了谢云因又如何?她是永安的好友,总归是会帮着她的,不管真相究竟为何,他一样知晓不了!既然如此,又何必知道?
两人之间原就只隔着数步与一张书案,满室的静寂之中,皇帝的脚步声越来越近。
岑樱吓得直哭,整个身子也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。正是此时,殿外忽然传进卞乐的声音:
“陛下,皇太子求见。”
伴随着这一声,皇帝如同从梦魇中抽离,脚步重重一顿,终于清醒些许。
“太子来了?”他转首看向门边。短暂的愕然之后,阴鸷双目赫然迸发出如狼的锐利,“太子怎么会来?!”
这一声有若熊咆龙吟,跪伏在地的岑樱又是一颤,眼泪再不受控制地滑下双颊。
“是。”卞乐侍立在门边,垂手而立,声音沉静听不出任何波澜,“陛下您忘了,您前几日召了太子来问河北道蝗灾的事。”
宣成帝如梦方醒,旋即忆起,似乎的确是有这么回事。只是他并没有约定是今日。
然而东宫与上阳宫相距甚远,他今日过来樱樱的寝殿是临时起意,就算太子提前得到消息也不可能及时赶来。
是他魔怔了,分明知晓樱樱有可能是他的亲骨肉,对着那张熟悉的脸,竟还是陷了进去……
“你起来吧。”
终究是还顾及着那一道血脉亲缘,皇帝神色复杂,看着地上纤骨颤栗不止的少女。
“今日之事是朕魔怔了,一时情不自禁。你只当没发生过,此后,你仍是永安县主,朕的外甥女。”
“樱樱,阿舅不希望你因为今日之事就与阿舅生分了,你可明白?”
他伤害了人,却还不许人介怀。岑樱从没觉得阿舅这个称呼如此可怕过,她害怕地垂着头,嘤泣着应:“樱樱明白了。”
这半日不过是强撑,当皇帝退出丽春殿后,她一个人怔怔地走回内殿,手脚冰凉。
殿中服侍的宫人早已在皇帝入殿时便被遣散,偌大的内殿只有青芝一人在,见她神色凄惶,关切地迎上来:“县主,您这是怎么了?”
县主。
岑樱怔忪地转首看她,她只觉得这个从那人身上得来的称呼十分恶心。而她在这偌大的宫殿里一个相熟的人也没有,此时遭遇了这样的事,连可以说话的朋友也没有,还要继续在这里待下去……
她想回家,她想阿爹,她不要再在这里了。
可她在洛阳人生地不熟,定国公府也不是她的家,她还能去哪儿呢……
岑樱越想越伤心,终于忍不住,扑在云母床上大哭起来,眼泪浸湿了重重被褥。
青芝一直耐心地抚着她的背柔声安慰着,等她哭声稍小了一些,柔声道:“县主,是想离开这里吗?”
岑樱直起身来,一开口泪水仍在簌簌地往下掉:“你有办法?”
话一出口又有些后悔,她什么底细她都不知道,如果她也是上回安福殿里那些要害她的坏人可怎么办啊……
她不能轻信于人。
青芝一笑,圆圆脸上梨涡浅浅,娇俏可爱:“奴叫青芝,上回在袭芳院,就是奴服侍的您,您还记得吗?”
“啊,是你……”岑樱恍然而悟。
“青芝姐姐,你怎么会在这里。”
青芝替她把眼泪新擦了擦:“是太子叫我来照顾县主的。”
太子……闷罐儿……
岑樱轻轻咬唇,眸子里水汽氤氲。
方才若不是他来了,圣人会对她做什么,她想也不敢想。
她昨日还想着他要娶那么多的贵女和他断了算了,现在却好想好想见他。她想他能带她离开,她真的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……
岑樱鼻子一酸,滴滴珠泪又似珍珠扑簌而落。青芝道:“县主若是想离开,奴倒有个办法。”
“这是太子殿下派人送来的蒿草花粉,若涂在肌肤上,便会起红疹子,连御医也能瞒过去。到时候,就说县主是病了,不适合再待在宫里。”
岑樱有些迟疑:“可我不想回薛家……”
薛家只有姮姮和薛鸣会关心她,可现在,她也不知道要如何面对姮姮了。
“那就去高阳公主府。就说县主思念姨母,想请高阳公主照顾您。”
岑樱听得愣愣的,最终轻轻叹了口气:“眼下,也唯有这个法子了。”
甘露殿外,嬴衍一身公服,孑孑独立,身影若松柏玉树的挺直。
他已在这里等候许久,漠然看着宫门上发亮的铜钉,目不斜视,心思却早已飞至了位于甘露殿西侧的丽春殿。
岑樱入上阳宫已经七日了,这七日间,他没有一日不似在火上煎烤。
阿耶想做什么他是知道的,岑樱却是个小傻子,只怕连男女之事也不懂。她又那么喜欢他,满心满眼都是他,若圣人当真不管不顾地强求,她如何应付得来?又该有多伤心?
今日就是他在中书省处理政务,却接到了卞乐派人送来的消息,言圣人叫人准备话本,其中有一册是《汉孝惠皇后外传》。
汉惠帝的皇后正是他的外甥女,圣人是何用意再明显不过。因而明知此举会惹得圣人猜忌,明知对她和他都没什么好处,但只要一想到那日高阳公主府里、她抱着他软软说想他的模样,他便什么也顾不得了……
她是因为他才被带来洛阳的,于情于理,他都不能丢开她不管。
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s://www.niumingzi.com/55105.html